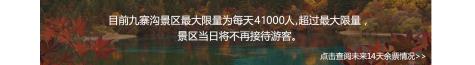一个留学生的理想与现实
这些年轻留学生们要面临的挑战并非是一个工作机会,而是带有美国工作签证的工作机会。
在纽约|张晶
毕业以后想从事什么工作?大概在刚入学的时候,她一定会信誓旦旦地对自己说,自然是跟媒体有关。
她就读的是美国一所不错的名牌大学的新闻学专业,虽然并非在纽约和波士顿这样的大都市,论师资论传统也能排得上前列。加之自身勤奋,GPA超过了4,前景一片光明。
但她却陷入了深深的惆怅。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暑假中,多份申请未果之后,她找到了位于波士顿的一间广告公司的带薪实习。校园里的小伙伴们都很羡慕 她,因为这些年就连找份实习都要挤破脑袋,很多还是无薪实习—有必要解释下,此前这个词往往存在于公益组织和电影圈,如今欠佳的美国就业形势已让它蔓延至 媒体和出版业、公关业还有臭名昭著的时尚业。
一进去她就发现梦想照进了现实。在那个小格子间里,她每天等着“指导老师”安排一些做PPT或者资料研究的工作,偶尔去旁听下公司与客户的会议。这和新闻发生时催生肾上腺素的时刻显然大相径庭。你也可以认为她是中了《广告狂人》的毒,总之没多久她就厌烦了这一切。
她总是在每个周末坐四五个小时的火车跑到纽约和文艺小伙伴们相聚,在布鲁克林的二手店和曼哈顿的艺术影院寻找慰藉。小伙伴A在美国排名前五的一 所学校里读比较文学。在A长大的那座城市,能进入这所学校读书的人每年以个位数计。但A却有着和她相似的失落感。“四年下来各种费用30万美元,而我却不 知道前途如何。”A向她诉苦。
那些从业十几年中途进修的年逾中年的记者,也因大报纷纷裁员而不得不转作自由撰稿,担忧着下个月或有或无的房租。还有美国劳工部的就业报告上的数字,20至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往往徘徊在10%。
听多了这些,她也会告诫自己说,现实一点吧,一鸟在手总好过十鸟在林。一个月的实习终于告一段落,“指导老师”对即将升入大四的她表示,“等来年再看吧。”
来年。有必要说一句,这些年轻留学生们要面临的挑战并非是一个工作机会,而是带有美国工作签证的工作机会。这往往跟一个称作“OPT”的东西相 关—在没有工作签证的情况下,它意味着毕业之后可以给予文科生12个月,理科生长达29个月的在美工作时间。而公司一旦要赞助工作签证,在雇员身上每月就 要额外支出数千美元,加之对媒体而言本地生不可比拟的语言优势,国际生往往被拒之门外。
带着失落的心,她又陷入了无日夜的勤奋学习中,虽然学的是新闻,但她开始攻克各类财务知识和计算机语言,前者自然是希望和有经济学背景的人争夺 《华尔街日报》、彭博社这类工作机会,至于后者,infographic和编程实在是这个时代的显学。她彻夜忙于做网站,将自己的经历和一些小成果制作成 活泼的网页,上面有各种可以被联络到的社交网络。
身边的小伙伴们都开始申请金融业的分析师、公关公司和各种各样的工作—中国人也给他们带来了机会,一个房地产商看准了美国南部某个州立大学附近的一幢楼,用60万美元买下重新改建装修转租给学生们,一个工作本来悬而未决的小伙伴因此获得了参与这个项目的工作机会。
但是她还是初心未改。最新的好消息是,她通过了彭博社第一轮的面试,随后彭博社将选定一个日期考试题目发给她,限制两小时内在线回答。在写了三篇文章之后,她发现最后一部分的要求如下,“讣告是新闻业中最重要和最具挑战的文体。请为自己写下讣告。”
她最终还是收了收想写下“这是历史上一个伟大记者”的心,用“因去底特律采访食物中毒而死的记者菜鸟”收了尾。
还是挺信誓旦旦的。像一块滚石。
张晶是本刊驻纽约记者
联系她请发
Email:zhangjing1@yicai.com